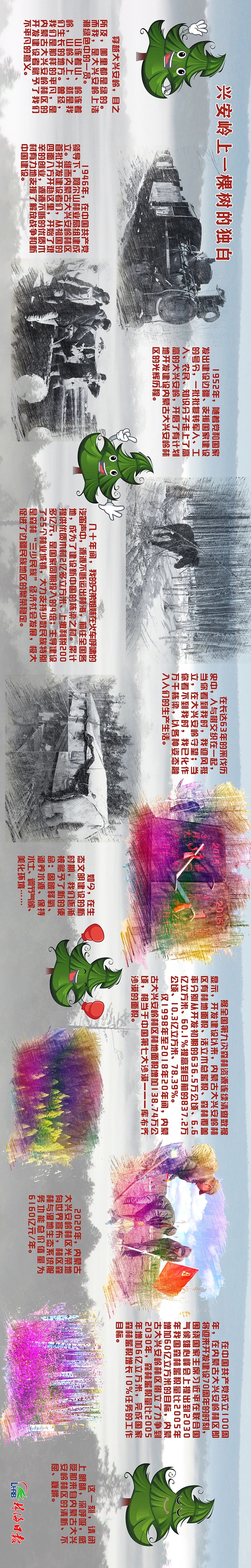興安嶺上一棵樹的獨白
穿越大興安嶺,目之所及,哪里都是綠的。而我,是大興安嶺上浩瀚綠色中的一員。
山連著山、嶺連著嶺,山嶺之上,就是我們生長的地方———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幽靜的后院。曾經,我們是那樣的平凡,是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的開發建設者賦予了我們不平凡的意義。
那是1946年,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,阿爾山林業局組建成立。繼而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首批開發建設者們,從祖國的四面八方開赴這里,爬冰臥雪、風餐露宿,開始了艱辛的創業,把青春和生命獻給了這片林海,把子孫留在了這里,一代又一代,揮灑熱血,無怨無悔,源源不斷的優質木材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建設。
1952年,隨著黨和國家發出建設邊疆、支援國家建設的號令,一批批復轉軍人、工人、農民、知識分子浩浩蕩蕩走上了高高的大興安嶺,踏進了茫茫的林海雪原,開啟了有計劃地開發建設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的光輝歷程。
一聲聲喊山號子響徹山林,萬里林海喧囂了起來,熱鬧了起來。從大肚鋸、彎把鋸到油鋸伐木,從牛馬套子到拖拉機集材,從人抬肩扛到機械化裝車,生產方式不斷改變,木材生產效率越來越高,幾十年間,我的兄弟姐妹也在火車呼嘯的汽笛聲中,源源不斷運出林海,前往全國各地,成為了建設新中國的棟梁之材。
篳路藍縷、以啟山林,在極其惡劣的自然條件下,開發建設者們克服嚴寒酷暑,戰勝雪嶺冰河,累計提供優質木材2億多立方米、上繳利稅200多億元,是國家同期投入的4倍; 主導建設了25個林業城鎮,大力支持少數民族特別是森林“三少民族”經濟社會發展,極大促進了邊疆民族地區的繁榮穩定。
“有多少省市用過這里的木材呀,大至礦井、鐵路,小至椽柱、桌椅。”1961年,老舍先生來大興安嶺采風時發出了這樣的慨嘆。
新中國成立之初,百廢待興,恢復生產、發展經濟成為國家在當時的首要任務。而我們在當時的作用超乎當今人們的想象。
那時,在礦井中,我們是頂梁柱,撐起了煤礦工人掘進采煤的通道;在鐵路上,我們是枕木,鋪就了物資運輸、人們出行的坦途;在供電、通信線路上,我們是線桿,為企業生產、日常生活輸送光明和便利;在汽車、火車上,我們是車廂擋板、座椅,乃至電氣包等零部件中也能我們的身影;在千家萬戶中,我們是房梁、地板、家具、鉛筆、紙張,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……
更令人難忘的是,在抗美援朝戰場上,我們被制作成手榴彈把、槍柄,隨著中國人民志愿軍雄赳赳、氣昂昂,跨過鴨綠江,經歷了兩年零9個月的浴血奮戰,拼來了山河無恙、國家安寧。
“千山一碧,萬古常青,恰好與廣廈、良材聯系在一起。”正如老舍先生所說,大興安嶺越看越可愛!它的美麗與建設結為一體,美得并不空洞,叫人心中感到親切、舒服。
這種可愛,這種親切、舒服,源自那興國安邦的“共和國長子”的忠誠,還有那把青春和熱血融進新中國建設的人們。
那時,林區條件異常艱苦,開發建設者住的是工棚子、地窨子,睡的是四五十人的大通鋪,吃的是水煮凍白菜,喝的是雪融水。“大雪壓青松,青松挺且直。”這對于我們的贊許,何嘗不是幾代務林人艱苦奮斗、無私奉獻的真實寫照。
在長達63年的采伐歷史中,人與樹交織在一起,當你看到我時,我迎風挺立,在大興安嶺守望;當你看不到我時,我已化作萬千棟梁,以各種姿態融入人們的生產生活。
如今,在生態文明建設的新時期,我們逐漸被賦予了新的使命:固碳釋氧、涵養水源、保持水土、調節氣候、美化環境……
在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,生態脊梁猶如那大興安嶺一樣,向來寬厚、挺拔。
據全國第九次森林資源連續清查數據顯示,開發建設以來,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有林地面積、活立木總蓄積、森林覆蓋率分別從開發初期的636.5萬公頃、6.6億立方米、60.1%提高到目前的837.2萬公頃、10.3億立方米、78.39%。
僅1998年至2018年20年間,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林地面積增加138.74萬公頃,相當于中國第七大沙漠———庫不齊沙漠的面積。
2020年,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光榮地向世界宣布,林區森林與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總價值量為6160億元/年。
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,在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即將迎來開發建設70周年的時刻,圍繞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氣候雄心峰會上提出到2030年我國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的目標,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樹立了力爭到2030年,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6億立方米,完成國家森林蓄積增長10%任務的工作目標。
這一刻,請閉上眼睛,深呼吸,感受那來自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的清新、不屈、巍峨。(劉洪林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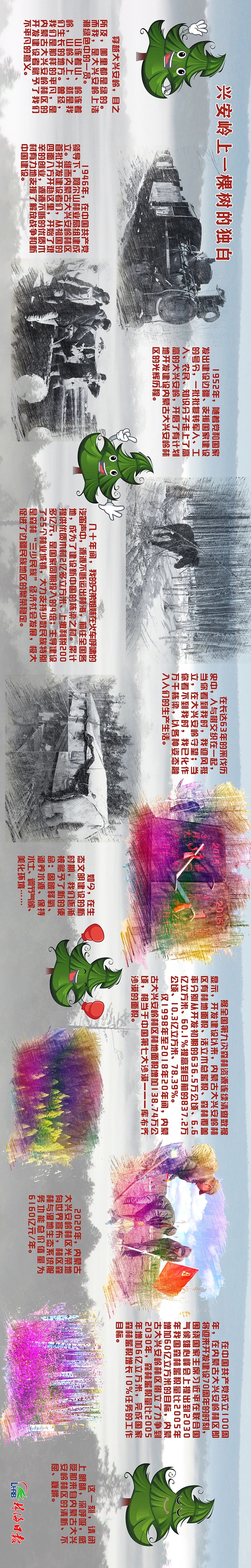


 郭衛巖
郭衛巖 2021-05-18
2021-05-18 3018
3018